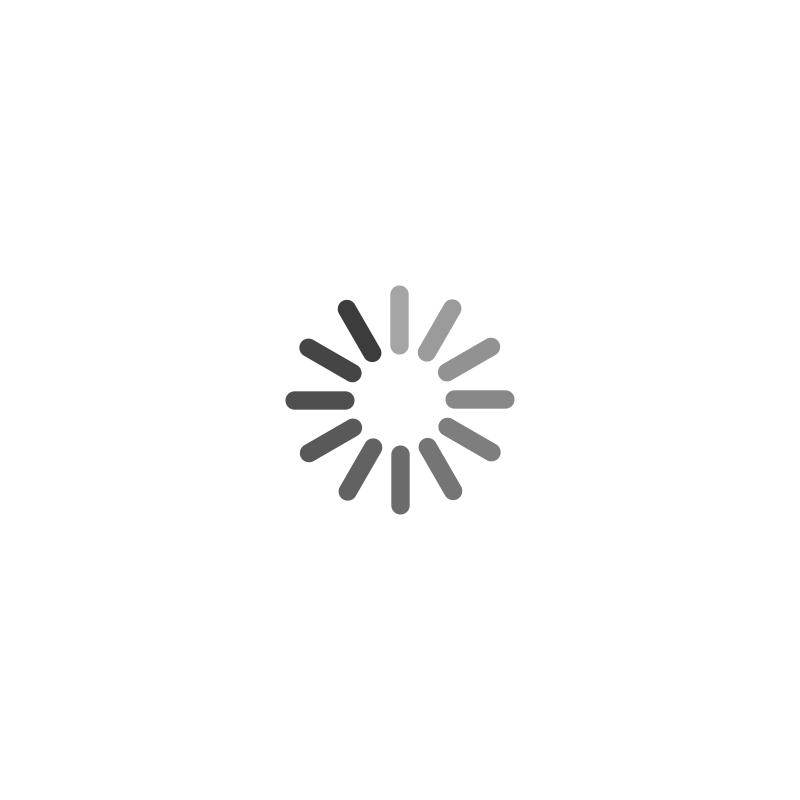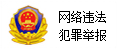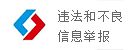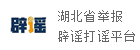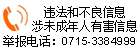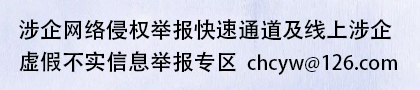第五次反“圍剿”斗爭(zhēng)的失敗和湘鄂邊中心縣委在崇陽(yáng)的建立(一)




“左”傾思想危害下的反“圍剿”斗爭(zhēng)
1933年9月,蔣介石在第四次“圍剿”失敗后,調(diào)兵遣將,對(duì)蘇區(qū)發(fā)動(dòng)第五次“圍剿”。從9月下旬開始,蔣介石調(diào)集100萬(wàn)軍隊(duì)、200架飛機(jī)開始對(duì)蘇區(qū)進(jìn)行大規(guī)模的軍事“圍剿”,其中以北路軍、南路軍30余師50萬(wàn)兵力圍攻中央蘇區(qū),以西路軍5個(gè)師另3個(gè)獨(dú)立旅10萬(wàn)余人圍攻湘鄂贛蘇區(qū)。敵西路軍第一軍軍長(zhǎng)陳繼承指揮第三縱隊(duì)2個(gè)師另3個(gè)旅“圍剿”修河(水)以北的鄂東南中心區(qū)。敵人的兵力除駐大冶的陳繼承第三縱隊(duì),駐陽(yáng)新的二十六師郭汝棟部,駐咸寧、通山的三十三師馮興賢部,駐通山、崇陽(yáng)的新十師謝彬部外,還有鄂南保安團(tuán)、各縣保安大隊(duì)、巡察隊(duì)、“鏟共”義勇隊(duì)等反動(dòng)地主武裝。國(guó)民黨采取修筑碉堡,移民并村,實(shí)行五戶一連坐和封鎖生產(chǎn)、生活、軍用物資等惡毒手段,妄圖扼殺蘇區(qū)革命根據(jù)地。僅崇陽(yáng),縣城的東西南北門就建有碉堡9個(gè),大沙坪2個(gè),白霓橋3個(gè),小沙坪2個(gè),還有洪下、桂口、東關(guān)、石城灣、桂花樹、高枧、鼓響嶺、塘口、黑橋、路口等地都建有碉堡。
1933年7月,紅十六軍在萬(wàn)載小源奉命改編為紅六軍團(tuán)第十六師,下轄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3個(gè)團(tuán)。高詠生、溫錦惠分別擔(dān)任紅十六師師長(zhǎng)、政委,仍為中共湘鄂贛省委領(lǐng)導(dǎo)下的紅軍主力。鄂東南紅軍及地方武裝力量也增加到5000余人。遵照湘鄂贛省軍區(qū)的命令,河南指揮部領(lǐng)導(dǎo)的贛北警衛(wèi)師編為紅一師(又稱“贛北師”),河北指揮部領(lǐng)導(dǎo)的河北警衛(wèi)師編為紅二師(又稱“河北師”),加上鄂東南紅軍主力紅三師,組成紅十七軍。8月1日,紅十七軍在通山黃石洞舉行成立大會(huì),軍長(zhǎng)張燾,政委方步舟,副政委兼參謀長(zhǎng)葉金波,政治部主任張向明。
為了粉碎敵人的第五次“圍剿”,中共鄂東南道委于1933年10月下旬在通山的石門楚王山召開道委擴(kuò)大會(huì)議,各縣、區(qū)委書記100余人出席會(huì)議。會(huì)議由中共鄂東南道委書記方步舟主持,中共湘鄂贛省委組織部長(zhǎng)吳致民參加會(huì)議,會(huì)上就如何組織鄂東南軍民進(jìn)行第五次反“圍剿”斗爭(zhēng)講了4點(diǎn)意見:一是明確鄂東南軍民的主要任務(wù)是牽制、打擊敵人,以配合中央蘇區(qū)的反“圍剿”斗爭(zhēng);二是加強(qiáng)蘇維埃政府工作,開展擁紅擴(kuò)紅運(yùn)動(dòng),壯大地方武裝;三是正確執(zhí)行肅反政策;四是收復(fù)失陷蘇區(qū),鞏固蘇維埃陣地。會(huì)議決定紅十七軍主力紅三師集中兵力,先收復(fù)龍港、燕廈、木石港等地蘇區(qū),然后向瑞昌、武寧等地發(fā)展;還提出了“打回龍港過(guò)年”的不切實(shí)際的口號(hào)。石門會(huì)議后,鄂東南紅軍主力紅三師向東南方向行動(dòng),咸蒲崇通縣獨(dú)立團(tuán)堅(jiān)持在楚王山的周圍山區(qū)開展斗爭(zhēng)。
對(duì)于湘鄂贛革命根據(jù)地極其嚴(yán)峻的形勢(shì)和長(zhǎng)期存在的軍事被動(dòng)、思想混亂和“肅反”擴(kuò)大化問(wèn)題,蘇區(qū)中央局早有察覺,多次致信、致電和派人巡視檢查,敦促中共湘鄂贛省委認(rèn)真解決。但是,省委書記林瑞笙等人極其頑固執(zhí)行“左”傾路線,對(duì)鄂東南革命斗爭(zhēng)造成很大危害。1933年10月,正當(dāng)鄂東南軍民奮起投入第五次反“圍剿”之時(shí),中共湘鄂贛省委工作檢查組來(lái)到鄂東南,全盤否定鄂東南軍民在第四次反“圍剿”中采用靈活機(jī)動(dòng)的游擊戰(zhàn)術(shù)所取得的成績(jī)。中共鄂東南道委執(zhí)委、中共通山中心縣委書記黃玉田因不同意紅軍“向東南發(fā)展,收復(fù)失陷蘇區(qū)”的決定和“打回龍港過(guò)年”的口號(hào),被指責(zé)為“右傾機(jī)會(huì)主義分子”,在通山石門坎同10余名優(yōu)秀黨員干部一起遭到錯(cuò)殺。檢查組還決定在鄂東南地區(qū)黨政軍組織中追查“改組派”,將鄂東南蘇區(qū)“肅反”運(yùn)動(dòng)擴(kuò)大化。
黃玉田等人被錯(cuò)殺后,中共通山中心縣委由新任通山縣委書記阮鳴鳳負(fù)責(zé)。阮鳴鳳貪生怕死,畏敵如虎,根本不能領(lǐng)導(dǎo)革命斗爭(zhēng)。加上中共咸蒲崇通縣委書記徐自然、梅經(jīng)武等人經(jīng)不住艱苦環(huán)境和肅反等考驗(yàn),1933年11月叛變投敵,導(dǎo)致整個(gè)鄂南工作處于停頓、被動(dòng)狀態(tài)。
1934年1月,蘇區(qū)中央局改組中共湘鄂贛省委,撤銷了林瑞笙的省委書記職務(wù),由陳壽昌接任省委書記。不久,省委派吳致民到鄂東南,調(diào)整中共鄂東南道委領(lǐng)導(dǎo)班子,調(diào)方步舟到省任巡視員,任命黃家高為中共鄂東南道委書記,并對(duì)所屬黨組織的領(lǐng)導(dǎo)人進(jìn)行了部分調(diào)整。1月8日,中共鄂東南道委召開紅三師與河北師、贛北師負(fù)責(zé)人會(huì)議,組成紅十七軍前敵委員會(huì),由張燾、葉金波分別擔(dān)任正、副指揮長(zhǎng)。會(huì)議按照“打回龍港過(guò)年”的計(jì)劃,決定集中優(yōu)勢(shì)兵力,先消滅木石港之?dāng)常謴?fù)周圍蘇區(qū),然后向東南發(fā)展,直逼龍港,進(jìn)圍武寧、瑞昌。1月中旬,紅軍主力及當(dāng)?shù)赜螕絷?duì)、赤衛(wèi)隊(duì)共近8000人攻打木石港,獲得大勝,恢復(fù)了木石港周圍的蘇區(qū)。接著又在木橋鋪等地重創(chuàng)敵軍,取得了局部的勝利。但是,局部地區(qū)的勝利并未從根本上扭轉(zhuǎn)根據(jù)地極其險(xiǎn)惡的形勢(shì),而紅軍在木石港休息7天,喪失了及時(shí)轉(zhuǎn)移到武寧、瑞昌一帶開展游擊,以避開敵人反撲的時(shí)機(jī)。1月下旬,當(dāng)紅軍1000余人南渡未成,回師黃沙,夜行至王文驛時(shí)遭敵伏兵包圍,紅三師除機(jī)槍連突出重圍外,其余人員全部潰散或犧牲,部隊(duì)損失三分之二。
由于紅十七軍主力紅三師在王文驛戰(zhàn)斗中損失較大,紅一師、紅二師解體,紅十七軍番號(hào)被取消,軍長(zhǎng)張燾被撤職調(diào)離鄂東南,副政委兼參謀長(zhǎng)葉金波先撤職,后逮捕被殺。在“左”傾路線的危害下,第五次反“圍剿”斗爭(zhēng)受到了極其嚴(yán)重的不利影響。